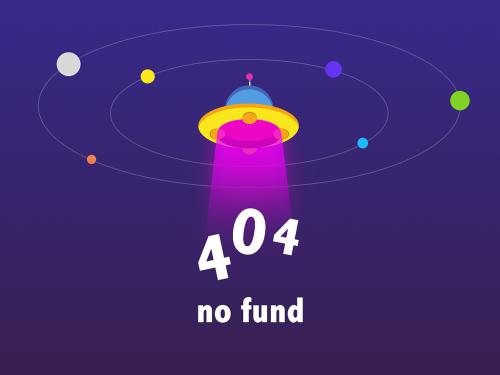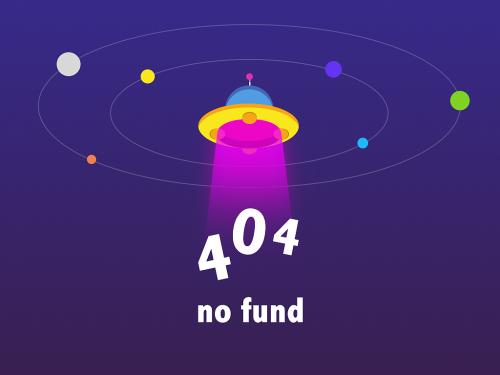-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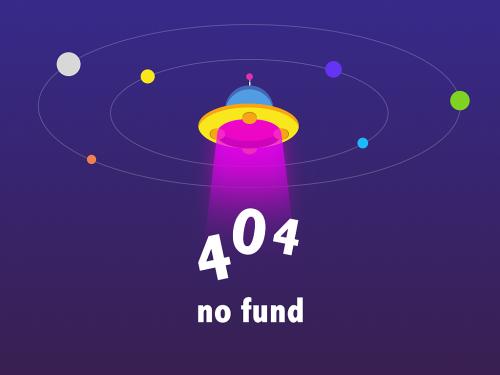
如何更大限度地避免“合成谬误”,更好提升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呢?今年10月,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提出“大田野”的政策研究方法,在这里或许能找到答案。
在《“大田野”的政策研究与经济学趋势》这篇文章的开篇,他这么写道:今人只知“大数据”,不知有“大田野”!其实,有关“大数据”,还存在一种广泛被大家忽略的现象,那就是“数字化的模糊”。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实际上也包括世界所有的国家在内,数据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数据驱动,这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数字化的模糊”。数字化的模糊是一种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数据越多,创造的这种模糊就越多。本来清楚的事儿,经过数字的一番修饰,你可能就会感觉它不对了,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的数据表明你的生活水平有了惊人的提高,你就会想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但从数据方面来看又确实如此。这就是数据的模糊。
这些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疫情当中,此次新冠疫情实际上揭开了很多事情的面纱,让我们透视了很多真实的一面。在过去,我们以为新冠疫情仅仅是一次流行疾病,过去也就过去了。但这次疫情不是,它带给人们、带给世界各国很多影响,有很多值得研究与反思总结的地方。现在的世界已经因为新冠疫情实际处于崩溃的状态,怎么从一个看似非常稳定的、繁荣的国家,接着很快就急剧转向一种不可琢磨的方向?天天看报纸简直吓死人,新冠疫情马上要杀死几万人、十几万人、几十万人···这种东西随处可见,这种说法也是随处可见。这么可怕、吓人的一种前景是怎么急剧出现转变的,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一个层面,就是数据的运用。
美国也公布了大量的疫情数据,但这种数据前后的矛盾太多了,甚至国家的、联邦的数据跟各州的数据都对不上号。死亡的统计口径也是一塌糊涂,最后只要检查出来有新冠疫情、有病毒存在,死亡原因就算是因为新冠疫情而死的,完全不管病人在整个诊疗、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否被传染。还有的人死亡在家里,并没有得到这种检测,那么就不包含,因此整体数据应是偏小的。像美国的cdc等等,这些统计都有很多的注明和说明,就告诉你我的数据不可靠,声明我的数据只能仅供参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所以美国的数据实际上也是相对的准确,并不是说绝对的准确。
这种例子实际上太多了,跟政治、社会相关的,凡是跟人相关的都会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所以才会说它是一种数字化的模糊。这种数字化的模糊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数字化模糊问题只能在研究过程当中,做研究的人不断地加以修正,一边做研究一边加以修正,保持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才可以形成一种真实的、可信度比较高的结果。
如果不是这样,保持一种绝对化的这种态度,面对这种数字化模糊,就认为是“我是基于数据的,我是基于模型的,我是在数据模型基础上得出结果的,那就是一定是正确的···”这只会闹笑话,只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世界银行最近连自己的《营商环境报告》都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在自我审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些数据的问题,那这下问题麻烦大了,连以前的从2018年开始的研究报告都不可靠了,都出现了问题。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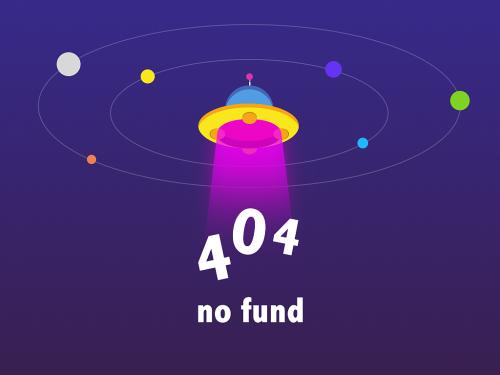
从世界银行的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数据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太大了,即便是权威机构也不能回避数据的这种缺陷,难逃数字化模糊的造成的后果。所以,跟许多教授不同的是,安邦是不太敢只用数据和数据模型来给领导写材料、写东西、写报告的。用个数据模型一说,就断定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是不敢完全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来做研究的。
让人遗憾的是,国内有很多机构、智库和研究学者,可以说过分迷恋图书里的经典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定量研究,而这导致公共政策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更遑论可形成系统化的政策。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大力提倡大田野调查研究,发展出自己的“大田野学派”,使得公共政策研究能提供更富建设性的支撑,助力系统性政策的形成。
“大田野”的政策研究方法?
陈功先生是“大田野”研究概念的提出者,也是始终奉行、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践行者,这才会有数十年来的安邦智库简报,才会有美国中西部的观察和分析,有上世纪的欧洲改革观察,也有本世纪的中亚研究。坦率地说,田野研究的概念,并非今人所创,中国也有一句劝学的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都是强调,田野研究与经典学术是同等重要的学术方法。
在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为独特精彩的一章,就是对调查研究之法的推崇和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脉络中最精彩的哲学篇章。“经世”一词最早可见于《庄子?齐物论》,谓之“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经世致用,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辈大儒倡导重视国计民生等社会现实问题,更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扎牢了根基。

在中国现代史上,“调查研究”始终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倡导的科学工作方法,是他一生所极力推崇的思想方法,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学术方法和研究基础。早在90多年前,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创作了体现求真务实精神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还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毛泽东在那时开展寻乌调查提出的经典论断。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也强调:“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关社会环境和公共政策的务实而精彩的传统中国学术之法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到了今天,已经从单人个体为重点的“调查研究”走向了强调规范性的“田野研究”;又从“田野研究”,走向了注重系统性和更大空间的“大田野研究”。所谓的“大田野”,实际就是田野研究的全系统、全空间的扩展。
对于田野研究,人类学是最成熟的科学应用领域。如果抛开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的人格缺陷来看他的学术方法,无法不承认马林诺夫斯基以田野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具有领先地位。正是在他之后,田野考察已经成为人类学最为突出的特征。现在的人类学,要是说一个人“没有田野”,或者说“田野不过关”,意思都是在批评这个人是不合格的人类学者,同时也包含着其作品不太具备专业信赖的意思。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特点来看,学术方法已经更为科学、更为精致,在地观点和实践的抽象和提炼、身份前提的设定、开放或者非开放的框架,都已经注入到了田野研究当中,使得田野研究更具科学价值和科学内涵。

图 |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参与土著生活的景象。「如果说查尔斯. 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原型人物,那么,勃洛尼斯拉夫.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便是人类学的原型人物」, 有人这么评价。
如果说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是为了通过研究异文化来反观“本文化”,空间主要是人;那么后来社会学的“现场研究”,空间已经有所推展,而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民族、文化、历史、网络、阶层、生活、产业门类等各种社会性的空间,都是“大田野”扩展后的天地,都是科学研究的现场。科学研究的大目标,从追寻大而宏观的“普遍真理”,再度回到了关注现实,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基础和变化,这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显著改变。
有趣的是,学术方法的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显著改变,必须要仰赖观察法和科学工具。观察法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这是一切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事实上,观察法是最简单的方法,但也是最复杂的方法。离开了观察法的基础训练,田野研究即便不能说是根本无法进行,但也会成为难度极大的工作,因此观察法是其它学术方法的根本大法。发展到今天,观察法的改变,只是在“方法的方法”方面。如果说过去的观察法,几乎完全依赖学者的个人学养和素质,那么今天的观察法,说到底还要依赖运用各种科学工具和方法的能力,比如数据统计。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以往格外强调经典、强调建立经典的维多利亚式学术领域——经济学领域,现在也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过去谈及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就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后来陈功向大家介绍“自然实验”方法的时候,基本没人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反映到当今的政策部门,情况同样很严重。长期受到教育体系误导的群体,很多人大脑中有一个并非正确的潜在意识,认为定量研究就一定比定性研究“高级一点”,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了。
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经济学方法的趋势走向,同样开始回归,同样在注重观察法的学科实践,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奖给了从事“自然实验”的经济学家卡德等人。

图 |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获一半奖项,另两位经济学家乔舒亚·安格李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因本斯(guido imbens)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共享另一半奖项。
所谓自然实验方法(natural experiment),实际是一种实证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对象处于研究者无法控制而由其他因素所控制的环境中,于是往往社会就成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大实验室”。只要问题聚焦恰当,设计巧妙,那么自然实验方法可以取得非常可信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自然实验不是对照实验而是观察性研究。
同样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对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做出评论和解释。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家通常无法进行受控实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观察。试图从经济观察中得出结论的麻烦在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例如,在比尔?克林顿提高高收入税收并减少预算赤字后,经济蓬勃发展,但这些财政政策是否带来了繁荣,还是克林顿只是幸运地“主持了”科技繁荣?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有另一种方法,即利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卡德与艾伦?克鲁格一起进行的关于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大多数经济学家过去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但这是真的吗?1992年,新泽西州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却没有。卡德(card)和克鲁格(krueger)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比较工资上涨后两个州的就业增长来评估这一政策变化的影响,主要是使用宾夕法尼亚州作为新泽西州实验的对照。这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卡德的原因,而克鲁格因为英年早逝,遗憾地没有获奖。

图 | 卡德(左)与克鲁格(右),1992年于普林斯顿大学燧石图书馆。两人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最低工资的重要研究,发现提高工资并没有减少就业。图片摄影:《纽约时报》frank c. dougherty
对于“自然实验”的方法,在国外,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研究近年来正在经历方法上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的统计推断转变到因果关系分析,学界甚至将其称为“可信度革命”。
与世界在学术方法上的积极演进相比,中国学术界在深与广两个维度上都有极大的欠缺。现在到世界各地旅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有不少年轻人,励志周游世界,从人迹罕至的瓦罕走廊,到非洲的原始丛林,现在到处都有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足迹。问题是与中国的年轻旅行者相比,这样做的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学者极少,他们依旧沉迷于“安乐椅”,津津乐道于西方图书馆中的所谓经典,以翻译和学生自居,习惯于由下向上看,仰视西方所有的一切。
这样的情况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刻,“大田野”不但应该得到普及和推广,要大兴调查研究,而且应该领风气之先,在中国发展成为“大田野学派”,凝聚、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充实各个学科,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和社会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原本就拥有这样的学术传统背景,今后是发扬光大和进一步创新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在“大数据”之外,还有“大田野”,这个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更为密切,与社会的发展命运更为密切,因此值得我们为此奋力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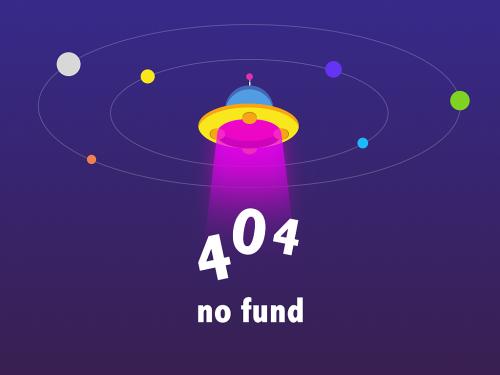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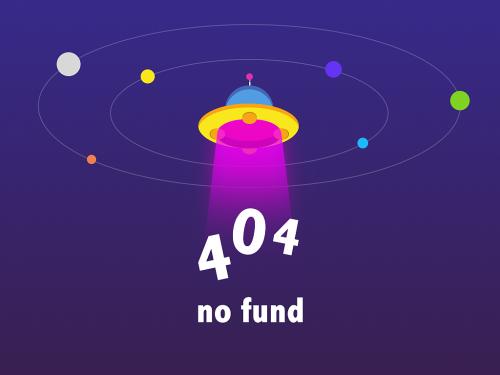
图 | 进行“田野研究”的陈功
“数字化的模糊”揭示了以“大数据”为主的定量研究和数据模型的缺陷。遗憾的是,国内很多学者过分迷恋图书里的经典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定量研究,忽略田野研究的重要性,导致公共政策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为此,中国应该大力提倡田野调查研究,发展出自己的“大田野学派”,使得公共政策研究能提供更富建设性的支撑,更好助力系统性政策的形成。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